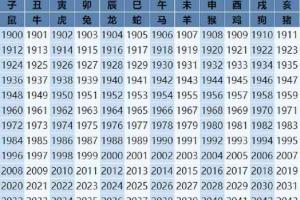法律要点:环境污染侵权中的因果关系证明
浙江省平湖师范农场特种养殖场诉嘉兴市步云染化厂等五企业水污染损害赔偿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06)民二提字第5号民事判决书
一、事实概要
嘉兴市步云染化厂等5企业长期超标排污,造成下游约53平方公里水域严重污染。原告浙江平湖师范农场特种养殖场(以下简称养殖场)位于5企业下游约6公里处,在水污染区域范围内。自1994年4~10月,养殖场饲养的美国青蛙蝌蚪陆续死亡。1995年12月,养殖场以受5企业污染侵害为由向平湖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赔偿损失,排除危害,停止侵权。养殖场提交环保处罚记录、水质检测报告、专家鉴定意见、其他养殖场证言等,证明养殖水域受严重污染,水质毒害致蝌蚪死亡。被告5企业则提交气象资料、个别养殖户证言等,认为污染并不必然致蝌蚪死亡,损害乃高温天气、原告技术等其他原因所致。
平湖市人民法院1997年7月判决认为:被告排污及原告损害属实,但原告的举证不能证实蝌蚪死于水污染,无法确定损害与排污之间存在必然因果关系,故驳回诉讼请求。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1998年10月二审判决认为,举证责任倒置仅针对过错证明,对于水污染造成蝌蚪死亡这一损害事实,原告仍须证明,故驳回抗诉,维持原判。2001年5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判决认为:根据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受损人需举证证明被告的污染物质排放及自身因该物质受损的事实,且在一般情况下这类污染行为能够造成这种损害。由于养殖场未对死亡蝌蚪进行解剖,不能证明其死亡系何种特定物质所致,未达到适用因果关系推定的前提,遂维持原判。
后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最高人民法院2006年提审此案,于2024年4月2日作出最终判决,认为“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作为侵权人的污染企业只有能够证明其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不存在因果关系或者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成立的情况下,始得免除侵权损害赔偿责任”,而本案被告“所举证据既不能证明其污染行为不会导致蝌蚪死亡,也不能证明蝌蚪的非正常死亡确系其他原因所致,因此对于本案中污染行为和蝌蚪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5家企业均不能提出足够证据予以否定”,故应当担责。
二、判决要旨
污染侵权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的适用与前提。
污染侵权因果关系证明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作为被告的污染者须充分确证其排污行为与原告所受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否则将承担败诉后果。但这一规则适用的前提是因果关系依常理看很有可能存在。
三、评析
(一)本判决的思路和意义
本案中,浙江三级法院均因原告未对死亡蝌蚪进行解剖,不能直接证明致害物质与被告排放污染物的一致性,以未证立必然因果关系或未达到因果关系推定的前提为由拒绝救济。最高人民法院的最终判决推翻了之前的错误处理。在确认排污行为和损害事实客观存在的情况下,法院跳过对原告所举因果关系相关证据的分析,重点审查“五家企业据以证明本案不存在因果关系的有关证据”,通过逐一分析,认为无法认定后,以被告未证立因果关系不存在为由判令其担责,从而阐明了举证责任倒置的规范含义和诉讼效果,为这一规则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运用提供了样板。但值得注意的是,本案原告在因果关系证明方面并非毫无作为,其提交的大量间接证据已达到证明因果关系“很有可能”的程度,这一现实背景是本案处理可谓成功所不可忽略的必要前提,也为后续司法解释明确原告的“关联性”举证义务埋下伏笔。
(二)环境污染侵权因果关系证明的规范及学理
污染损害的复杂性决定了其因果关系证明的困难,减轻证明要求、降低证明难度是各国的法律通例,但具体做法不一。多数国家从减轻证明负担的角度处理(胡学军:《环境侵权中的因果关系及其证明问题评析》,载《中国法学》2024年第5期),我国则主要以举证责任倒置应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1992)22号](以下简称《意见》)首开先河,规定环境污染诉讼中“对原告提出的侵权事实,被告否认的,由被告负责举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第4条进一步明确污染诉讼中“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类似表述为2004年修订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86条、2008年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第87条所复制,并为2024年通过的原《侵权责任法》所效仿。该法第66条规定“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成为污染侵权因果关系证明的主要规则。《民法典》第1230条只是增加了“破坏生态”的情形,同时将“污染者”改为“行为人”,在证明规则上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
然而,前述规定到底意味着什么,学界认识不尽一致,大致分为三类观点:一是“举证责任倒置说”(王社坤:《环境侵权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分配研究-兼论(侵权责任法》第66条的理解与适用》,载《河北法学》2024年第2期);二是“因果关系推定说”[杨素娟:《论环境侵权诉讼中的因果关系推定》,载《法学评论》2003年第4期;程啸:《侵权责任法》(第2版),法律出版社2024年版,第578页;杨立新:《侵权责任法》(第4版),法律出版社2024年版,第317页];三是主张二者兼备的“复合论”[王利明:《侵权责任法研究》(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第492~496页;周友军:《侵权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第389~390页]。
从广义角度,宽泛而论,举证责任倒置对被告如不能证明因果关系不存在将败诉的处理隐含着“推定”因果关系存在的意味,故二者常被混为一谈。但从诉讼理论和实践效果来看,“因果关系推定”与“举证责任倒置”又有本质差异:前者是一种事实认定的方法,举证责任仍按“谁主张,谁举证”由原告承担,只是证明程度有所减轻-只要达到一定程度即可推定因果关系存在而无需达到通常要求的“必然”程度。此时,被告也可能因为不能成功证明“因果关系不存在”而败诉,但这种证明属于“反证”,以原告先已成功举证为前提,且证明标准通常较“本证”为轻。后者则意味着法律直接把“不存在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分配给被告,其须作为“本证”充分证立,否则将承担败诉后果,且不以原告先行证立为前提。
在实践层面,折中调和的“复合论”显然无法成立。从前述条款的字面表述和充分保护受害者的立法目的来看,“举证责任倒置说”颇具优势。但其适用条件过于宽松,存在逻辑缺陷,“基本上使被告无机会翻身”[薄晓波:《倒置与推定:对我国环境污染侵权中因果关系证明方法的反思》,载《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6期],有矫枉过正之嫌。故在理论界,“因果关系推定说”更受认可。应先由原告证明被告排污与己方受损之间的初步关联,再由被告承担因果关系不存在的举证责任。但这一认识与现行法清楚、明确地“倒置”规定不甚相符,其作为主流观点使理论应然与立法实然产生张力,加剧了司法实践的纠结与困惑。
从本案来看,最终判决也体现出理论选择上的矛盾与纠结。尽管表面看来,法院以举证责任倒置为论证核心,强调“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作为侵权人的污染企业只有能够证明其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不存在因果关系或者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成立的情况下,始得免除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并以被告“没有足够的证据否定其污染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为由判其败诉,似乎在充分践行“举证责任倒置说”。但其在最终提出举证责任倒置角度的推论之前强调“位于上游的五家企业污染了水源,同时段,下游约六公里的养殖场发生了饲养物非正常死亡的后果”这一实际上表明因果关系“很有可能”的适用前提,又不无“因果关系推定说”的影子。
(三)既往司法实践状况
尽管立法对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具体且清晰,但司法实践呈现的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实证研究表明,环境民事案件中“运用举证责任倒置的不足半数”(吕忠梅等:《中国环境司法现状调查-以千份环境裁判文书为样本》,载《法学》2024年第4期);即使有所运用,也“在大部分情形下仍然由作为受害人的原告承担因果关系成立与否的举证责任”(张挺:《环境污染侵权因果关系证明责任之再构成-基于619份相关民事判决书的实证分析》,载《法学》2024年第7期)。这其中,既有地方法院“重发展、轻环保”的传统观念甚或地方利益作祟,也有认识不清、学艺不精的能力问题,但也不乏基于司法操作现实的合理考量。总体来看,法院在环境司法方面认识不断深化,重视不断加强,态度渐趋开放,但对纯粹的举证责任倒置始终抗拒,其能接受的最大限度,似乎只能是“宽松的”因果关系推定,此在本案跨度十余年的历次审判中得到充分展现。
在1997年的初审判决中,平湖市人民法院完全依传统规则判案,要求原告证明“必然的因果关系”,完全无视《意见》的存在。在1998年的二审判决中,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举证责任倒置仅针对过错,把“水污染造成青蛙蝌蚪死亡”视为仍须原告举证的“损害事实”。在2001年的再审判决中,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虽然认可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但还是从“因果关系推定论”角度的理解,认为“受损人需举证证明五家企业的污染(特定物质)排放的事实及自身因该物质遭受损害的事实,且在一般情况下这类污染环境的行为能够造成这种损害”,继而把蝌蚪死亡“系被何特定物质所致”作为“适用因果关系推定的前提”。
类似的处理,在实践中并不鲜见。在“孙大年诉新沂市通力氨基酸厂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案”中,法院认为“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前提是死鱼样本存在可供鉴定。目前由于样本不存在,无法鉴定的责任在孙大年,故孙大年未能完成初步举证责任,如简单适用举证责任倒置,不仅有违立法本意,且对于通力厂也显失公平”[徐州中院(2006)徐民一终字第27号民事判决书]。在同样历经4次审判、受到包括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内的多级检察院抗诉而由最高人民法院指定重审的“刘德胜诉湖南省吉首市农机局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案”中,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最终判决仍以“由于目前无法准确界定各种癌病的起因,在此情况下,如果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以市农机局举证不能为由推定本案所涉市农机局环境污染行为与刘德胜患癌病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必然因果关系,缺乏事实依据”[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6)湘高法民再终字第102号民事判决书]为由判令被告败诉。或许正因为该案的刺激,最高人民法院在面对情形类似的本案时没有再发回地方,而是亲自审理、彻底改判,就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含义及如何适用作出明确指引。
然而,如前所述,本案处理“正确”的前提是因果关系确有可能,而这种可能性是通过双方证据的“攻防”共同形成的。一旦场域转换到可能性不那么大的情形,一旦失去双方举证这一必要机制,仅仅举证责任倒置的推导还能否做到公平公正、让人信服,不无疑问。随着相关探讨的增多,以及越来越多地方“抵制”的披露,最高人民法院已认识到纯粹举证责任倒置的缺陷,开始要求原告适度举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加强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的意见》[法发(2024)11号]要求原告“提交污染行为和损害之间可能存在因果关系的初步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4)12号](以下简称《环境侵权司法解释》)更明确要求被侵权人证明其损害与污染者排污之间的“关联性”,在司法规则层面向实质上的“因果关系推定说”转向。
(四)本判决的参考意义及将来的课题
本判决中,法院对举证责任倒置操作的演示,以及对被告如未证成即须担责的强调,都具有积极意义。但制度层面的真正价值,却在于对本案实施举证倒置的现实背景-“位于上游的五家企业污染了水源,同时段,下游约六公里的养殖场发生了饲养物非正常死亡的后果”一的阐述。这一表述背后隐含的“依常理很有可能”,既关乎举证倒置的前提条件,又指向“关联性”证明的具体判准,正是解决此类案件最需明确的关键。遗憾的是,判决未就此做正面阐述、集中论证,而是急于挥舞倒置大棒,从而丧失了一次明确界定“推定”标准与“倒置”前提的良机。在《环境侵权司法解释》要求原告证明“关联性”却未做具体指引的情况下,法院在因果关系判断上仍有过大空间,不无滥用隐患,犹待未来破解。
四、参考文献
王利明:《侵权责任法研究》(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
周友军:《侵权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
程啸:《侵权责任法》(第2版),法律出版社2024年版。
杨立新:《侵权责任法》(第4版),法律出版社2024年版。
杨素娟:《论环境侵权诉讼中的因果关系推定》,载《法学评论》2003年第4期。
王社坤:《环境侵权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分配研究--兼论(侵权责任法>第66条的理解与适用》,载《河北法学》2024年第2期。
吕忠梅等:《中国环境司法现状调查-以千份环境裁判文书为样本》,载《法学》2024年第4期。
薄晓波:《倒置与推定:对我国环境污染侵权中因果关系证明方法的反思》,载《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6期。
胡学军:《环境侵权中的因果关系及其证明问题评析》,载《中国法学》2024年第5期。
张挺:《环境污染侵权因果关系证明责任之再构成-基于619份相关民事判决书的实证分析》,载《法学》2024年第7期。